1 min to read
“反应停”事件

版本1
1953 年联邦德国一家制药公司合成了新药“反应停”(酞胺哌啶酮),1956年开始在市场试销,1957年获本国专利,随后在全球51个国家获准销售。在市场推广初期,该药在怀孕早期妇女止吐方面显示了很好的疗效,且未发现明显的毒副作用。然而,1959年12月联邦德国儿科医生 Weidenbach 却报告了一例女婴的罕见畸形;1961年 10月,三名联邦德国妇科医生也发现了类似的缺少臂和腿的畸形婴儿,手和脚连在身体上,很像海豹的肢体,故称为“海豹畸形婴儿”。后续的研究证实了这些畸形婴儿是妇女在怀孕初期服用“反应停”所致。截至 1962年,全世界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共报告了1万余例海豹畸形婴儿,仅联邦德国就超过 6000 例,英国超过 5000 例。这是 20世纪最大的药物导致先天畸形儿的灾难性事件。1962年以后,国际社会禁止把“反应停”作为孕妇止吐药物,仅在严格控制下可用于治疗癌症、麻风病等。就在“反应停”声名狼藉之际,一名以色列医生却偶然发现“反应停”对麻风结节性红斑有较好疗效。1998年,美国FDA 批准“反应停”可作为治疗麻风结节性红斑
反应停在市场销售中一波三折的惨痛经历意味着:新药研发具有潜在的高风险,上市药品的安全性需要追踪考察;同时,特定药品或许会有其他方面的疗效。因此,在新药临床试验过程中,受试者/病人是否充分知晓潜在的风险?是否真正自愿参加?当新药在市场销售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不良事件,制药企业应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这是新药临床试验和应用中伦理决策和伦理审查的重要内容之一。
针对生物医学研究、临床实践中引发的伦理问题,20世纪 70年代以来兴起的生命伦理学有较为全面的回应。 进入 21 世纪,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学、基因伦理学、护理伦理学、公共卫生伦理学等分支学科得到快速成长。同样,针对生物医药工程实践中伦理问题的识别和分析也就成为工程伦理关注的热点。简言之,生物医药工程伦理学是一门以生物医药工程中引发的伦理问题为导向,识别伦理问题的表现,辨析其特点、根源和后果,结合相应的伦理学理论、原则和方法,开展伦理分析论证,并提出伦理建议的新兴学科。
版本2
20世纪50年代末,德国药厂格兰泰公司推出了沙利度胺(商品名“反应停”),一种止吐药,广泛用于缓解孕妇的晨吐症状。该药物迅速进入多个国家的市场,特别是在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等国。根据该药品的宣传,它被认为是对孕妇安全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报告揭示了令人震惊的副作用:服用该药物的孕妇所生下的婴儿普遍出现先天性四肢缺陷,其中最常见的是海豹肢症——一种导致四肢发育不全的致命缺陷。此外,沙利度胺还被发现会影响眼睛、耳朵、心脏和生殖器官等其他器官的发育。
这一情况的严重性逐渐浮出水面,但直到1961年,格兰泰公司才停止了沙利度胺的销售。尽管如此,已经有大约1.2万名畸形儿诞生,且数千名孕妇因服用该药物而遭遇流产。在这场灾难中,唯一未受到影响的国家是美国,因为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药品审查员弗朗西斯·凯尔西博士拒绝批准沙利度胺的上市。她的坚持保护了美国市场的安全,避免了类似灾难的发生。
格兰泰公司在得知沙利度胺的危害后,仍未愿意承担责任。公司的态度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愤怒,尤其是在那些因药物而承受巨大身体和心理痛苦的家庭中。直至2012年,格兰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才在一次公开演讲中首次为该事件道歉,承认药品对新生儿健康的重大危害,并表示对未能及时采取行动深感遗憾。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沙利度胺事件的责任和赔偿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决。尽管格兰泰公司从未正式承担责任,社会各界依然持续关注这一事件,并对受害者及其家庭表示深切同情。在2023年11月,澳大利亚政府正式通过设立国家纪念馆,并由总理和卫生部长共同发表公开道歉,承认“沙利度胺悲剧”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的“黑暗篇章”。政府希望通过这种举措,帮助受害者在情感上获得一些治愈,尽管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痛苦。
此事件揭示了药品研发、销售和监管中的重要伦理问题,特别是关于药品安全、公司责任以及政府监管的角色。在全球范围内,它催生了对药物审查和批准过程的更严格要求,并促使多个国家加强对公众健康的保护。
讨论问题
- 该事件中涉及的各方(药品公司、监管机构、消费者、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
- 在药品上市前,如何平衡药品的潜在益处与其可能带来的风险?
- 如何有效提升监管机构在确保药品安全方面的作用,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 药品公司应如何对因其产品造成的严重后果承担社会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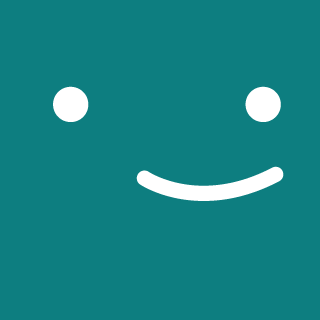
Comments